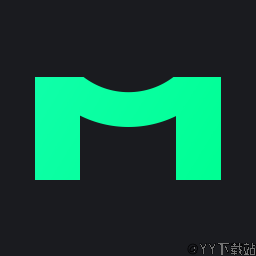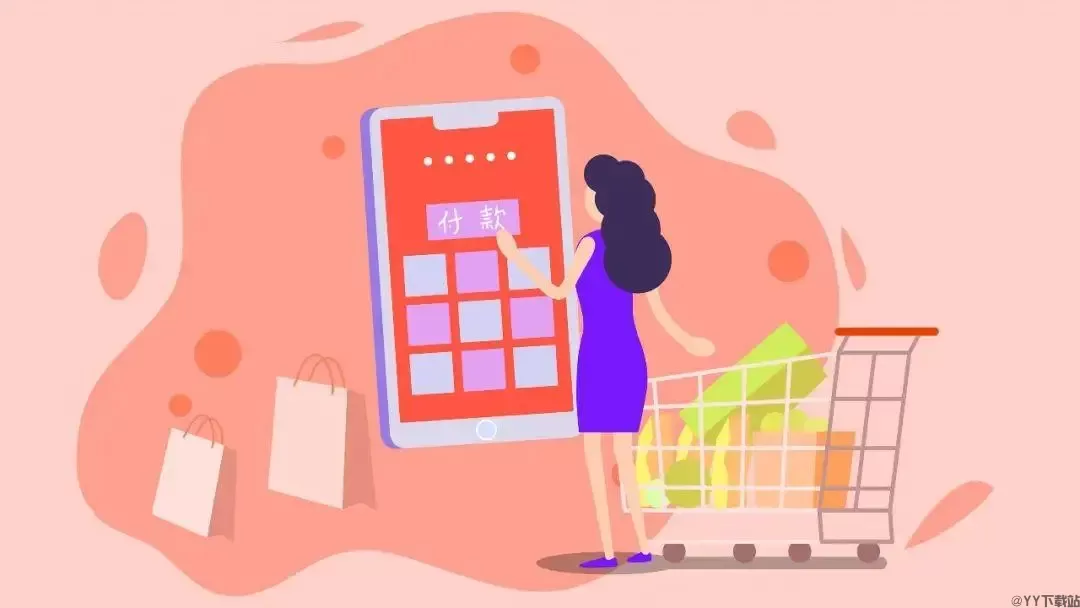暗色作战塔布羊缰绳,大 漠 寻 马 记。
大 漠 寻 马 记
作者:张肇韵
题记:青春殇逝,如同沾满血渍的青苹果,坚硬苦涩;残酷得如幻觉,却又真实到极致。时光荏苒,岁月蹉跎,那既苦涩又幸福的记忆彷佛就在昨天,纠结着我的心灵。追忆那似水的流年韶华,寻觅那凋零的葳蕤残叶,回味那往昔的峥嵘岁月,犹如一叠叠浪花击醒绚丽的水帘,又如草原上蒙古包前的篝火点燃了激情的火焰,等我回来,来拥抱蓝天......
领受任务
1972年初春,那一年,我刚满17岁。我从一排一班调到后勤排饲养班,与老职工马志忠师傅一起放羊。没多久,饲养班的一匹二等红枣溜马失踪了,同时一匹灰色两岁口的马骡(注:马骡是母马生的骡子)也不知去向。
丢失的红枣溜马是团部生产科分配给十连的,当时分配给十连两匹马,丢失红枣溜马是其中的一匹。当时国家规定:牧区一等马匹供应军队,二等马匹供应兵团和地方(计划经济年代,生产资料及物资都按计划分配供应)。当时二等马价格是280元/匹(当时每个兵团战士生活津贴费5元-7元/月),同时丢失的两岁口马骡,按当时价格就得上千元。
这事可真急坏了连长和指导员。连队大牲畜属固定资产,丢失必须向团里汇报。那是在“文革”中期,出了这种事情,责任之重可想而知。处理轻则是定性领导对连队管理不严,重则很难预料,饲养班班长、后勤排排长,“当家人”连长、指导员,都难逃其责。记得当时连长孙宝玉只说了一个字:“找”。
十连地处乌兰布和沙漠边缘,任何大小牲畜经过都要留下不同痕迹(蹄印),连队职工中有两名打踪(追踪)能手,一位是马志忠师傅,另一位就是当时马车班的王维达师傅。二位师傅确定了失踪的马和骡子的蹄印及行走方向,一路向北沿伸追踪二十几公里,蹄印在风沙过后越来越不清晰,方向是向北,再向北……离我们十连向北百十公里就是阴山山脉(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大青山),中国有句老话叫“老马识途”,莫非失踪的红枣溜马出生地在阴山山脉北部的草原?那可是中蒙边境地区潮格旗呀!
寻马任务连队领导交给了我。到潮格旗寻找丢失马匹的决定通知了我,现在可能还会想想为什么决定让我去?可当时作为一名兵团战士没有为什么,也不会去想为什么,战士的职责就是执行命令听指挥,头脑简单,一切事情自然也就变得简单了!这次外出与我共同执行任务的另一位是我们十连小学的杜老师(那生杜力格尔)。杜老师是蒙古族,蒙汉兼通。中蒙边境潮格旗,是蒙古民族游牧聚居地区,办事交流首先靠语言,只要语言能沟通,才能过寻马下落的“第一关”,连队领导考虑周全啊!
寻马上路
准备工作非常简单:首先连队开出“通行证”再到团里开张“介绍信”,从会计那支出几十块钱差旅费,一切就都齐备了。个人所准备的物品那就更简单了---水壶、书包、毛巾、肥皂、自备大衣,走那住那,虽说已进入5月,但阴山北部还是很冷的。
第一站由连队到杭锦后旗(陕坝)公安局,拿出“通行证”换取边防证(潮格旗是中蒙边境地区,只有拿边防证才能买到去潮格旗的长途汽车票),那时,杭锦后旗到潮格旗的长途车每天只有一趟。杜老师与我买到了班车最后的一排座位,那可是比打“站票”强多了。破旧的班车,坑洼不平的土路,把后排的人颠起来头撞车顶,又重重地跌落,五脏六腑好似移了位置,现在的柏油路很难再尝到这种感觉了!过去的土公路,晴天是洋灰(扬灰)路,下雨时是水泥路。破旧的长途班车到处漏风,车外扬灰,车里车外灰蒙蒙一片。经过半日的颠簸,乘车人个个灰头土脸,上台唱戏不用化妆全都够“花脸”水平。
五月份的潮格旗,也就是初春的感觉,只要太阳一落山,身穿棉大军衣都不热。一眼望去除旗政府的一些办公院落,其它就是一些平房,这里全无繁华热闹可言,一切都觉得那么冷清。所谓的街面上,只能见到几掛马车或拴在路边的几只骆驼及马匹,行人不多,看着都那样懒散。夜晚的旗招待所,靠柴油机发电的不稳电压,使本来就不明亮的电灯泡忽明忽暗,远处传来断断续续的狗叫声,使人听起来更加烦躁与不安。下一步该怎么走?丢失的马匹和骡子到哪去找?
第二天一早,杜老师与我到潮格旗畜牧局,根据马匹调拨日期查了一遍马匹调拨地,大致范围圈了四个公社,记得是潮格公社、那仁宝力格公社、巴音前达门公社和莫林牧场,再具体到那个公社那个大队则不得而知!天啊!就这四个公社占地就有几千平方公里,找丢失的马匹如同大海捞针。
当年的牧区,牧民过的都是游牧生活。人走家搬,一顶蒙古毡包,一辆木头轱辘的牛拉勒勒车,哪的草场好,牲畜就往那赶,别看今天住这儿,明天又不知搬到哪里去了。那时的生产大队,只有一排或两排固定的砖坯房,这里最吸引人的地方就是小卖部,小卖部里最受欢迎的商品也就是低档的卷烟,散装的白酒,砖茶,食盐……。计划经济年代商品匮乏,一是老百姓兜里没有钱,二是国家底子薄,物资极度缺乏。牧民如想买点像样的东西(如添件衣物或买布)那就得骑马跑上近百公里到旗所在地供销社去采购。
杜老师与我面对占地面积几千平方公里的四个公社,真的没“咒”可念了,进退两难,进如茫茫大海捞针,退回连如何交代!俩人商量半天,走哪算哪,找到哪算哪!那时由潮格旗政府到下面公社的班车,每周只有一趟,只要赶不上你就只有再等一个星期,两人心急如焚,最后咬牙下决心,凭着两条腿寻吧!
面对茫茫戈壁,虽说已进入五月份,仍然显得那么凄凉。低洼背风的地方绿色刚刚显露尖尖小角,戈壁荒滩黄色主调仍然压抑着萌发的绿色。无风的日子天空显得很蓝,只要起风,虽不能说飞沙走石,但也够天昏地暗。有时走半天或一天也见不到一户人家,别说按顿吃饭,就是想找口水喝也难,累了走不动了找个背风或能晒太阳的地方坐一坐或躺在地上伸伸腰,缓过劲来,再继续走。
当年的潮格旗,没有固定的围挡的草库伦,很少见到成片的马、牛、羊群——洁白的羊群像珍珠洒落在绿色的草原,那是歌词中的赞美,也可能是内蒙古自治区东部地区的草原与西北部的荒滩戈壁真实的距离。有时候走一天还真能见到十只八只为一群的黄羊。这些“精灵”远远的瞪着大眼睛望着我们,时刻保持着高度的警惕和有效的逃跑距离,只要我对着它们做出端枪的姿势,口中再“砰”的一声,转眼之间黄羊会逃得不知去向,当时暂时的开心快乐,精神为之一振,冲淡了劳累之苦。现在回想起来,国家野生动物保护法要是早出台30年,黄羊在内蒙地区也不会濒临绝迹了。
与杜老师在潮格旗凭两条腿行走寻马,回想起来还真有点浪迹天涯的味道。那年我不满18岁,杜老师也就二十五、六岁,说精力那是充沛的。在蒙古民族居住区不会说几句日常的蒙语,别说找地方睡觉了,就是想混口饭吃,讨口水喝也都难。一路上我不断地向杜老师请教蒙语会话,见面第一句话就是“塞拜诺”(你好的意思),下面跟着就是自我介绍,从哪来、干什么、吃饭、喝水都学会了,剩下的事也就好办了!如果你不会说几句简单的蒙语,只要对方用蒙语说“咩得快”(不知道)或者说“吾贵”那可就全瞎了!别想蹭吃蹭喝,你就是用全国粮票花钱买也没有。当时就是靠着杜老师这位蒙汉语言兼通的拐棍,走到哪还都有口饭吃,有口水喝……,至今我还能说几句简单的常用蒙语。
当时我与杜老师身上所带的文件证明一是连里开出的通行证,二是团部开出的找马证明信,三是杭锦后旗公安局办理的边防证,这三件“法宝”还真起到了关键作用。记得在五月底,潮格旗所有地区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严格盘查所有到边境地区外来人员,民兵、边防部队持枪,见人就严查,没有边防证及介绍信的就地扣留,后来才知道,山西军分区副司令员余洪信,因私人恩怨矛盾开枪打伤副政委及打死副政委妻子后逃跑,为防止从中蒙边境逃跑出境下发了通缉令,这在“文革”期间也算重大事件吧!(注:余洪信自毙遗体最终在山西一片庄稼地里找到。)
艰辛寻马近一个月的时间里,走到哪吃住到哪,忍饥挨饿。当地牧民的生活也非常艰苦,那里没有蔬菜,主食就是炒米(炒米就是将糜子米炒熟),放在碗里用奶茶(砖茶加羊奶或马奶兑水加盐熬制成茶)加盖泡制,将炒米焖软食用。遇到家里有“菜”的牧民,从泡菜坛子里取出一点夏天挖的野菜(加盐泡酸了),上好的是拿出半个又咸又酸的芥菜疙瘩切来待客就很不错了!至于肉食,遇到生活好的牧民家,你可以享受到去年秋天宰杀的风干的生羊肉条,主人拿出一条又黑又硬的风干生羊肉,手拿蒙古刀将肉干削成薄片放入炒米中,再用熬好的奶茶一起冲泡焖软食用。当时的我怎么都想不通,风干生羊肉为什么不加工熟了再吃?干羊肉片用奶茶能泡熟吗?这样的吃法到胃里再加工能受的了吗?最后咬牙闭上眼睛瞎吃吧!别忘了入乡就得随俗。
记得在我们找马期间杜老师与我吃到一顿最丰盛的大餐,是在潮格旗边防连。那天边防连队打了一只野骡子(估计是野驴),野骡子什么样没见到,但煮熟后的大块肉是吃到了,又黑又粗的肉丝,嚼起来很费劲,夸张点说如同饿“狼”见到了肉,拼命将自己的肚子填饱,那可吃的真叫个香啊!
蒙古民族喝酒吃肉是生活习俗。说到喝酒,一天杜老师与我走到一处放牧点,放牧点有三位蒙古族兄弟,我们说明了来意,三位主人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中午,他们拿出一只装满酒的铝水壶,分别倒入缸子(搪瓷杯)和大碗内,平均分配,人人有份,大约连20分钟都没过,酒过三巡,各个见底,菜过五味那可就睁眼做梦啦!刚刚喝起酒兴,酒就没了,怎能善罢甘休?!其中一位牧民,说他那里还有两瓶酒精。我一听就急忙说酒精不能喝,三位牧民说他们兑水喝过,没问题。在坚持不住的情况下,我问清最近牧业大队小卖部的方向,骑上他们放牧的骆驼,向能买到酒的大队小卖部奔去……。回想起来,当时自己年龄小,借着酒劲,也不知道什么叫害怕,骑着骆驼一路狂奔,大约跑了二十公里路程,见到戈壁荒滩中的几间土坯房,这儿就有小卖部,这就有花钱能买到的散装白酒。我来不及等骆驼跪下再下来,抓住驼峰从骆驼身上直接溜下。当我背着灌满酒的行军水壶再次骑着骆驼按原路返回,还没跑半路,想不到的事情了,远处出现了驼群,我骑的这匹骆驼,见到驼群直奔而去,不管你如何拉牵鼻绳,它就是原地转圈,再也不向回家的原路走一步。折腾了一个多小时,骆驼从口里喷了我一身臭烘烘的反刍黏液,最后我投降了,把骆驼牵鼻绳盘好,放它回归骆驼群了,剩下十几公里的路程,只有靠自己的两条腿“拐”回去啦!
经过半天时间的折腾,当我背着买到的白酒回到牧业点住地,眼前的情景让我惊呆了---四个男子汉东躺西卧,土炕上、地上吐得乱七八糟,当时只有杜老师还清醒,我一看就知道他们一定等不及我买回来的白酒,把那两瓶酒精喝光了,这也可能算是“男子汉”的豪爽吧!
第二天,男子汉们的酒劲过了,人也清醒了,我把骑骆驼买酒的经过及骆驼归群一事向他们说明,大家一听都笑瘫了。他们惊讶我北京来的兵团小战士胆子够大,并跟我说这匹骆驼是参加潮格旗那达慕骆驼比赛大会跑的第二名的家伙,一般人还真难以驾驭,看来当时我应该属于“二般人”了,小男子汉的地位开始确立了。
第一次找马到潮格旗,吃、住都是难题,走到哪吃到哪,临行时按兵团的纪律留下粮票和饭钱,那时的粮食是按人头供应的,谁都只有自己的那一份,只要回想起计划经济时代的清苦,才能感受到改革开放后生活的变化。
在潮格旗找马时的住宿问题,现在回想起来当时就像流浪汉,走到哪,自然就住在哪里了,无论是蒙古毡包还是牧业点的土坯房,晚上找个靠边的地方和衣而卧。那时牧民家里谁家都没有多余的被子,自然也就是自带的军大衣替代了。一个月的牧区“流浪”生活,无处洗澡,无处换衣服,脸脏了就找点水洗一把,再想讲点其它卫生,那可就是奢望了。时间一长自然就招来了不速之“客”,虱子、跳骚已成常“客”,见怪不怪。“小动物”养的实在太多了,也有办法,弄点六六粉或敌敌畏洒上,“小动物”也害怕,能逃命也就逃命了,农药的气味难闻,别说“小动物”就连大活人都呛得难以忍受,看来要想讲究卫生,那还真要付出点代价…….
历时一个月,凭借两条腿,我们走遍了四个公社,徒步行程大约五、六百公里,口头颁布寻找丢失的马、骡子告示,走到哪儿,“发”到哪儿,打听到哪儿,就这样把最原始的广告传遍四个公社地区几百平方公里,效应是在几个月之后才出现的!
二度寻马
杜老师与我在潮格旗一个月的寻找丢失马、骡,经历了说不清的辛苦,最终仍无下落,只能无功而返,回连队复命!当时的心情很差,情绪非常低落,完不成连队领导交办的任务,回连怎么交代?可确实找不到丢失的马、骡,也不能呆在潮格旗不回连队吧?当时我是“光棍”一个,自己能吃饱了连耗子都不饿,可杜老师就不同了,老婆、孩子都在家里等着呢!既然如此还是回连队再说吧!
回连复命,说明找马经过,连长、指导员并没有因我们未完成任务给予责备。越是这样我内心越自责,最终的怨愤都发泄给随身带回的“小动物”们啦!在饲养班用煮马料的大铁锅烧开一锅水,将全身衣物统统扔了进去……
回连队大约三、四个月(也就是1972年9月份)之后,喜讯传来:团司令部通知说,十连丢失的马匹和骡子确实跑回了潮格旗,消息是从潮格旗畜牧局传回来的。确实是喜讯,这说明了杜老师和我在潮格旗的罪没有白受,凭借两条腿和口头“广告”起作用了!
连长孙宝玉再次找我,让我与马车班老职工王维达再次去潮格旗。这次心里有底了,也看到希望了。简单准备行装,本人行军水壶里灌满的也不再是水,而是牧民最爱喝的白酒。这也就是为了尽快完成任务特意准备的秘密武器“糖衣炮弹”吧!
一到潮格旗,我与王师傅就通过潮格旗牧畜局查询,确定了连队丢失的马匹和骡子跑回的公社、大队后,我们就直奔目标,最终在该大队一个姓王的牧业点确认了此事。
这是一个五口之家牧业点,一对中年夫妇,带着两女、一儿,居住在一间十多平米的低矮土坯房内。房内土炕占据了多一半空间,土炕的一角是全家人烧火做饭的锅台。长年做饭烧水烟熏火燎,房顶的檩条和椽子被烟熏得又黑又亮。本来用泥土抹的内墙,长年被烟熏成了棕黄;土炕上铺着几条灰黑色的羊毛毡,也不知用了多少年。靠在墙边码放着叠成条的三、四床棉被;唯一的家具是一个可以搬来搬去的小炕桌,一家人吃饭可以围坐在一起。屋里唯一能采光的窗户没有玻璃,取而代之是粘贴着各种不同的纸(破了随便找张纸糊一糊),只要不漏风就行了。白天关上屋门,屋里就像黑窑洞。这里没有电灯,没有半导体收音机,没有……如同与世隔绝,外界信息只有来人口头传递。
姓王的牧业点主人是外来到潮格旗落户的汉人,后来结婚生子,扎根在茫茫戈壁荒滩。此人身材高大,少言寡语,但在与家人说话交流时用的都是蒙古语(也许他的妻子就是蒙古族)。他们的生活经济来源是为大队放牧马群(约有百十匹马)。计划经济年代所有牲畜都是集体所有,而个人一无所有,就如农业地区不允许有“自留地”,彻底割掉资本主义尾巴,你也就一心为“公”了。长年的清贫生活,见不到贫富差距,世人相同,肚子能填饱,衣服能遮体,就能生存,至于其它,孩子生病怎么办?小孩到哪里上学念书等等,不用问看也看明白了。
在与牧业点主人见面时,我们说明了寻找连队丢失马匹、骡子的来意,主人并没有感到突然,一切好像在情理之中,也如同知道早晚会有人找上门去。他听我们说完,轻轻的点点头说,由他马群调出的马,确实跑回来了,而且还带回一匹灰色马骡。话语间透出了一份自信和自豪。接着他又说,跑回来的马和骡子在他们的牧群里替我们代牧半年多时间啦!
牧业点王姓主人与我们见面交谈几句之后,再不多言,两三天过去了,就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样。有时他骑马出去一趟很快又回到家里,至于什么时候把我们连丢的马和骡子套回来只字不提。我们心急火燎,却又无可奈何!遇到这种事,催不能催,急又不能急,哎!
时间一分一秒的就这样过去了,过了一天又一天。我也不断在琢磨着牧业点主人的那句话:“跑回来的马和骡子在他们的牧群里替我们代牧半年多时间啦”。难道这是暗示要跟我们算“工钱”吗?在文革期间,计划经济年代,没有什么私有之说,作为兵团战士,可以说就连生命都是国家的,只要国家需要,人民需要随时都可以奉献;如谁有一己私利或一闪念,那将会受到谴责和批判!那个年代任何人的头脑中没有经济利益,也没有个人得失,国家既有内债,又有外债,底子薄,老百姓自然清苦要受穷。对我个人来说,当时头脑简单,造就四肢还算发达,可就对人家主人“暗示”的这句话楞琢磨了两天才明白过味来!此事要是放在改革开放搞活市场经济的今天,恐怕十岁的孩子都能明白这个道理:只要有付出就要得到回报!
当时我们两人身上都加到一起也就几十块钱和几十斤的粮票,再就是身上的衣物。我后悔二次到潮格旗找马,没有把困难想的多一些,以为只要带够路费、饭钱也就足够了,所以也没有跟连长、指导员提任何其它要求。眼前的一个简单小事,一下子变得复杂了很多。怎么办?再回连队请示拿钱根本不可能;打个长途电话或发个电报那要到潮格旗邮电局,往返几百公里路程,首先得赶到公社所在地,还得要赶上每周一趟到旗所在地的班车(长途汽车),看来还是行不通。此事要是放到现在,那自然再容易不过了,从兜里掏出手机往连里打个电话说明问题就结了!可是在1972年“手机”这个词都没有出现,别说我们国家就连资本主义国家也还都没有出现这个“产”物。那时的老百姓,谁家要是有台半导体收音机能收听到电台广播,也是让人非常羡慕的奢侈品了。时代的进步,科技的发展,国富民强,一切由过去的不可能变为今天的可能,看来“只有想不到的没有做不到”的这句名言,在人类科技高速发展的今天,一切皆可变为现实。
怎样回报牧业点主人?确实让我和王维达师傅为难,也想不出好的办法来解决。心里难以抑制的烦躁,不停地围绕这间低矮的土坯房外围转圈。房后面不远处有一口人吃畜饮的大口土水井(土水井的结构是用草和柴禾一层一层从井底压上来的)。因地制宜,是人类生存的技能,这里没有砖,也不可能用砖砌筑水井。在离土水井不远处码放着一垛土坯。就是这垛一直没有放在眼里的土坯,让我看到了希望的光亮。经了解,牧业点主人一家五口常年居住在这间十来平米的小土坯房,两个女儿已都十几岁了,实为不便,想再盖两间土坯房,家中又缺少壮劳动力,平时主人抽时间挖点土,脱些土坯,但离盖两间房的目标相差甚远。脱大坯、挖土、挑水、和泥、脱坯、晾晒、码放,那可都是力气活,要想盖两间土坯房,最少也要2000块土坯。潮格旗地处中蒙边境,冬季气温低,风沙大,异常寒冷,所以从保温来讲,房屋墙体的厚度是必须的。
“出卖劳动力,脱坯换工”!我们将这个想法与主人一沟通,自然“目标”不谋而合,他那少言寡语的脸上露出一丝让人不易察觉的得意。俗话说得好,“傻小子睡凉炕,全凭火力壮”。虽然这次出来钱没有带够,但力气还是有的。信念只有一个:卖力气能把连队丢失的马匹、骡子换回来也值得!
说干就干。谁知事情总没有想的那样简单容易。戈壁荒滩上的土含有碎石,光凭拿铁锹那可真得费点力气。挖了半天也没挖出多少土,手上很快就磨出血泡,脚底登铁锹,脚掌生疼,到了晚上身上如同要散架。王维达师傅也有五十出头了,一老一小,答应承诺的事情,必须兑现,决不能退缩,一定要咬牙坚持。第一天挖土的晚上我在炕头边上和衣而卧,盖上军大衣很快就进入了梦乡……
戈壁荒滩的九月底、十月初,早晚的天气很冷,中午虽气温较高,但脱出的土坯块两三天都干不了,这就需要倒换脱坯场地。从原有坑中挖出的土,需要运到新脱坯场地,没有运土的车,只能一筐一筐的抬,无形中又增加了工作量。为了加快和泥速度,脱鞋光脚在泥里踩,坚硬的碎石时常会把脚扎破划伤,几天下来两个人脱坯的双手裂开了一道道的血口。
流血、流汗、吃苦、劳累,现在城市里长大的孩子身居楼房冬暖夏凉,从无经历,也无需经历,只有经历过那段历史的人,记忆永远都不会从心中抹去……。
今天,我自己的女儿已到而立之年,可我从未向她谈及自己的过去。如果说了,她们也一定认为我们这一代人冒傻气,自找苦吃那是乐意,为什么不早点离开兵团去闯自己的一番天地?历史已成为过去,记忆却深深埋藏在自己心底!
经过七、八天的艰苦努力,王维达师傅与我脱出的土坯已够盖两间房了。牧业点主人面带笑意的说,你们歇一天,我明天就把你们的马和骡子套回来。主人没有食言。第二天的下午,他与另外一个牧马伙伴真的将马和骡子套了回来。我和王维达师傅一看,丢失的骡子没错,但是马已经不是原来连里丢失的那匹红枣溜马。问其原因,主人回答说:那匹跑了几百公里穿过阴山山脉的红枣溜马回来不容易,主人自然也不愿意放手再让我们带回去。怎么办?请示连长、指导员,征求是否同意?那根本是不可能的。反过来一想,反正连队大牲畜头数够了,管它红马还是黑马,是马就成!这就是我第一次斗胆做了连队领导的主。俗话说得好,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就是大尾巴狼也得“充”一回。
驯马归来
见到套回来的马匹和骡子,说实话那一瞬间心中确有说不出的滋味,酸甜苦辣全都涌了出来。丢失的马和骡子经历了辛苦磨难终于找到了,找到了……,即将完成寻马任务,返回连队指日可待了!此时此刻,恨不得骑上马插翅立刻飞回连队……!
就在我想入非非的情景中,牧业点主人问我和王维达师傅会骑马吗?惊醒中我连忙说:会骑,会骑!主人接着说那你骑给我看一看。我没加任何思索,当时也不知道全身哪来的一股横劲,翻身跨上马背。哪料想自己屁股还没在马背上坐稳,马一低头一个尥蹶子就把我从马背上扔了出去!在大家哈哈大笑之中,我顾不上挨摔的疼痛和狼狈相,急忙从地上爬起来,口中还硬充“好汉”:“没关系,再来、再来!”说实话本人自北京到兵团还真在连队骑过马,什么连里通信员骑的小红马、花屁股马,那可是训出来的马呀!对于其它的牲畜凡是能骑的不能骑的,驴、骆驼、牛及至连里的种猪、种羊都尝试骑过,甭管骑上走多远,哈哈一笑,年轻孩子没事淘气寻找开心吧,枯燥的连队生活,平时没事只有自己偷着找乐子……
牧业点主人见我挨摔的样子,对我说你等等,看我怎么骑这匹没被人骑过的马。说罢只见他翻身上马,双腿牢牢夹紧马的肚子,任凭这匹黑马怎么折腾、尥蹶子,如同一块膏药贴在马背。我生平第一次明白为什么人称蒙古地区的牧民为“马膏药”,那驯马的能力、技巧就是不一般,再烈的马,在他们的手里也会驯得服服帖帖。黑马折腾了大约20分钟,筋疲力尽,主人拿出马鞭在马上不停的抽打,接下来黑马在戈壁荒滩上狂奔,几圈下来,黑马浑身颤抖汗液顺着马腿滴滴嗒嗒往下淌,接下来就是马粪、马尿拉了一地,再瞧这匹可怜的黑马原有的精气神全没有了,低头搭邋脑袋,鼻孔中不停的喘着粗气。牧业点主人将已驯服的黑马缰绳交到我的手里,对我说现在骑上它再接着跑几圈。当我再次骑上马背,黑马的原有狂傲刚烈荡然无存,怎么使唤怎么听。此时我心中暗想,真是神鬼怕“恶人”啊!接下来溜马、梳理鬃毛,自然也都是我去干了。
连队丢失的灰色马骡,别看身架高大,却生性胆小。王维达师傅骑上去,没折腾几下就老实了。
找回马和骡子的当天晚上我们就开始做返回连队的准备,来时没带马笼头,马嚼子。笼头可以在牧业点主人家找材料做两副,马嚼子是铁匠打的,哪去找铁匠?没有就没有吧!
第二天一早,王维达师傅与我问清穿越阴山最佳行走路线(不可能沿能走的公路返回连队,那样走太绕远,要多走三、四天),并按兵团规定给牧业点主人留下粮票和饭钱。两人分别骑上马和骡子,按牧业点主人所指的方向,向阴山山口而去。当我离开那间低矮破旧的土坯房,不时的在马背上回头远望,心中涌出一种说不出的滋味。我见证了文化大革命计划经济年代牧民的生活清苦和寂寞,他们在这片贫瘠的戈壁荒滩上深深扎下根,世代繁衍生息…….
经过一天的行程,我们骑着没有鞍子的马、骡远离了戈壁荒滩,到达了阴山山脉北部山口附近。这里人烟稀少,费了很长时间才找到一户人家,说明来意,求宿一晚。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情况挺有意思,清苦的生活在牧区无论你走到谁家,无论蒙古毡包,还是院落,家里有人没人都不锁门,一是家里穷的只有两三条能盖的被褥,算是值钱物,再就是吃饭所必须的锅碗瓢盆,顶多再有一把熬奶茶的铝壶、铜壶、炕桌、脸盆之类的东西。那时候的牧民都非常豪爽好客,见行路人有困难只要你求助,一般家庭还都能帮你,也许那时的诚实、本分是做人的基础,清贫家无财物,自然也就不怕“贼”惦记。
第二天一早,爬起来才感觉到骑了一天马的浑身酸痛,像要散架。王维达师傅已五十出头,夜里为了照顾我,能让我睡个好觉,他要经常起来照看马、骡子,一是别再让它们逃跑,二是将它们喂饱。现在回想起王维达师傅在同行中处处关心我、呵护我,虽然话语不多,但他那办事认真、细心,吃苦耐劳、为人和善的样子,让我至今难以忘怀!
拖着疼痛的身体,还有那被马背磨得快要掉皮的屁股和双腿,一瘸一拐,继续赶路。屁股疼的不敢坐,走路就像“鸭子”步,那样子,多亏当时没让十连战友看见,要是看见,准能笑的爬不起来。
当我们来到山口走进去一看,这里确实有一条小道,时宽时窄,走人和走牲畜还可以,但走不了车,说白了就是一条“茶马古道”。两山之间的山坳里小道如同蜿蜒的细线高高低低,时而走进那曾被山洪冲刷过的干枯河床,时而走进那悬崖峭壁的两山缝隙之间,这里没有人烟,也不会找到能歇脚的住家“驿站”,大山里死一般的寂静,只有我们自己的脚步声和马骡蹄声。中午时分,我早就饿得前心贴后背了,两人身上除了有壶水,再没有可以吃的东西,那可真是张飞拿耗子——大眼瞪小眼。饿了喝口水,饿急了还是只有喝口水……。这时远处悬崖峭壁上出现了一只青羊(野羊),居高临下远远的注视着我们。此时,我大喊一声,转眼青羊跑的不知去向,这也好提起点精神继续赶路。在我们即将走出山口时,在山崖上又发现了一只团羊,长着一对磨盘一样的犄角---这就是它“战斗”与逃生的武器,高高立在山崖之上,那雄壮的身躯,威风凛凛。这种野生动物,我只见到过这一次,后来王维达师傅对我说讲,团羊如遇到危险,可团在一起利用犄角保护身体,从山崖上直接滚落,这也是团羊生存的本能。现在不知阴山里是否还有这种野生动物生存?
在夕阳的余辉下,我们终于走出山口,眼前的河套大平原一片金黄色展现在眼前,激动的心情,早已把挨饿的肚子忘记在脑后,拉着马匹拼命地向山下平原奔跑……,找到能行车的公路,天就完全黑了下来,这样我们心里也就踏实了。沿着公路继续南行,远处发现闪烁的灯光,总算找到居住的人家啦!拉马走近一看原来是兵团四团连队,见到他们就如同见到亲人一般,在兵团战友的指引下,我们来到饲养班,把马和骡子拴好,喂好。战友们从食堂为我们打来饭菜,这时王维达师傅和我早已饿得过劲了。
这一夜,在四团连队饲养班睡的那叫香甜,如同睡在自己的“草窝”里。一觉醒来已日上三竿,连队早饭时间已过,战友们还是为我们留下些馒头。为了赶路程,也不可能再等吃午饭,有这两个馒头足够了,谢别四团连队战友,骑上马、骡继续赶路。
进入秋季的河套平原路旁的景色要比戈壁荒滩好看多啦!能见到的树木、叶子还是绿色,田地里的庄稼,泛着金黄,太阳照在身上暖洋洋的。多日的奔波劳累不知不觉让我骑在马背上慢慢的闭上了双眼,乏困带我进入了梦乡。
当我再次听到马的嘶叫声时,身体早已腾空而起,接下来是重重的跌落在地。当时,我还没反应明白怎么回事,只见黑马掉头拖着缰绳飞奔而去……。此时我顾不得挨摔的疼痛,爬起来向马奔跑的方向追去,无耐,两条腿怎么也追不上四条腿,转眼间连黑马的影子都看不见了。这时的王维达师傅骑着骡子早已掉头去追黑马,我一路边跑边走,心里那叫悔恨,眼看就完成的任务,就像煮熟的鸭子要飞啦!这匹可恨的黑马如果再跑回潮格旗,找马所付出的辛苦可就全“泡汤”啦!此时后悔、乱想全没用,追,就是舍出命来,也得把马追回来!
大约向相反方向追了十几公里,远远看见王维达师傅骑着骡子,牵着马向我走来,此时我心里又一次激动,眼泪就落了下来,多亏了王维达师傅,要是没有王师傅,这次找马会付出的代价更多!这次我挨摔马跑的原因是,经过路边水渠的水闸,哗哗的流水声让没有见过世面的黑马受惊,本人挨摔是小事,完不成任务可是大事,幸好有惊无险。
这次突发事故,来回一折腾半天时间又算白瞎了!为了防止再出意外,王维达师傅让我换乘骑骡子,他骑马。第三天的晚上,我们已到达离连队几十公里外的公地公社附近,为了安全起见,只有找地方再住一宿。
第四天的中午,我们穿过连队北部的四坝公社塔布大队,牵着马、骡站在高高的沙丘之上,看见了我那日思梦想的三团十连营房,从沙丘的顶上牵着骡马连滚带爬冲向连队,到家了,总算熬到家了……。
后记:两进潮格旗寻马经历,一晃已过去38年。这只是兵团生活的一个片段,至今在我脑海之中每一幕仍是那样清晰历历在目。今日我将这一小段兵团生活寻马经历奉献给当年同甘共苦的战友,只有当年的纪实,也用不着华丽词句。现人已都过中年,留下只有回忆。当年所经历的磨难,也是我终身的“财富”,在以后的工作生活中,再没有任何困难能挡住我向前的脚步……
注:
1、第一次与我同行到潮格旗找马的小学校老师杜那生,后来由十连调到五原县公路局。大约在1980年前后,我在内蒙古建筑勘察设计研究院工作,帮助设计勘察五原县自来水厂时,曾去看过他一次,后来也断了联系!
2、第二次与我同行到潮格旗找马的王维达师傅,在赴内蒙兵团四十周年回到第二故乡三团时,从他儿子王智贤口中得知老人已去世!
( 2010年3月于北京)
相关阅读
- 碧血晴天,千娇百媚一颗痣,娱乐圈几位“痣美人”,谁最有味道。[07-11]
- 原神松木,原神:零氪深渊挑战第九天,林尼的伤害还不错。[07-12]
- 英雄联盟声望系统抽奖活动地址( 1天20万声望)[08-05]
- 华为u8860刷机教程( 国产手机发展史:锤子手机)[08-05]
- 绀田村东北方的荒废神社,原神在荒废神社中继续调查攻略 任务人影顺序一览。[07-11]
- 八神连招,拳皇97:最终boss大蛇到底厉害在哪?。[07-12]
- 盗贼宏,wow经典怀旧服法师盗贼宏推荐。[07-11]
- 鸿蒙专题报告:系统开天辟地,生态千帆启航[07-10]
- 幻想神域钓鱼,正统官方续作《幻想神域》手游版正式宣布。[07-12]
- 白色烟雾照明弹,烟雾弹是士兵的辅助工具,一起来体验一下烟雾弹#烟雾弹。[07-12]
- 绿宝石386,GBA中文游戏超大合集。[07-11]
- 无冬之夜3,这个栽在腾讯搜狐手上的工作室,曾经是外国人眼里的中国之光。[07-12]
- 画中世界流程攻略( 画中世界)[08-05]
- 大型网络游戏排行榜2013前十名( 有你的青春吗?盘点中国网游史中那些里程碑网游,你玩过几款呢?)[08-05]
- 华为MatePad SE标准版平板将预装“无阉割”版鸿蒙4系统[07-01]
- 恶魔的气息,成龙历险记八大恶魔实力排名,谁是你心中的第一?。[07-12]
- 阴阳师周年庆,阴阳师周年庆福利问题 阴阳师周年庆福利分析。[07-11]
- 十字军图纸,魔兽怀旧服实用附魔图纸详解。[07-12]
- 九重试炼合成表,九重试炼法宝图鉴攻略。[07-11]
- 龙之谷pk,龙之谷手游哪个职业pk厉害 pvp职业推荐。[07-12]
热门资讯
-
山屋惊魂,《承传》设计师与威世智的天作之合《山屋惊魂》即将推出Legacy。
2024-09-22 00:02:54 -

恶魔巫师出装,搞趣网:全民超神邪火神怎么出装 邪火神出装攻略。
2024-09-22 00:01:07 -
妖狐试图掳走的妖怪是谁,聊斋故事:引 魂。
2024-09-21 23:58:01 -
无尽之剑3刷钱,我们是金币搬运工!《魔兽世界》怀旧服猎人刷钱盘点(副本篇)。
2024-09-21 23:55:53 -
阴阳师蝴蝶精,阴阳师:R卡团宠蝴蝶精迎来新皮,你的钱包准备好了吗?。
2024-09-21 23:54:04 -
梦幻西游转区要多少钱,闷声赚钱时代已过今日揭露梦幻西游转区商人的暴利生活。
2024-09-21 23:50:16